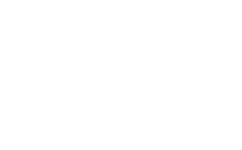在国外,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environmental safety ;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 。我国不少人往往将外文中原本具有不同含义的环境安全,都译成为没有差别的环境安全。其实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管理这类安全的政府机关或组织主要有卫生部门、劳动安全部门、产品或技术监督部门。笔者将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由于与生产技术活动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各种有害影响,人们开始使用环境安全的说法,这时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即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安全问题;这种环境安全仍然是指对人的健康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人传递不安全影响的中间物即介质。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认识的深化,一些环境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赋予环境安全以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安全和卫生安全的新的含义,即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也确认环境安全问题也是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这样,环境安全就成了一种与原有的劳动安全、卫生安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的安全概念;当然,这种环境安全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技术性安全的范畴。
对于技术性环境安全问题,各国立法都很重视。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有关生产或劳动安全、技术安全、产品安全(尤其是农药安全、有毒化学品安全)、交通安全等的法规和标准已经相当健全,不少环境法规都有关于技术性环境安全的规定,在制定环境标准时大都将保障安全列为首要的或基本的目标。例如,美国迄今已经制定《联邦煤矿安全健康法》(1969年)、《职业安全和卫生法》(1970年)、《饮用水安全法》(1974年)等生产技术性环境安全的法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将技术性的环境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规定“保证为全体美国人创造安全(safe)、健康、富有生产力并在美学和文化上优美多姿的环境”、“最广泛地合理使用环境而不使其恶化,或对健康和安全(safety)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它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从国际范围看,目前已经制定诸如《关于职业安全、职业卫生与工作环境的公约》(1981年)、《石棉安全使用公约》(1986年)、《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1990年)等技术性安全公约或法律政策性国际文件,在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标准中也有技术性环境安全的内容。《21世纪议程》第34章,就“环境安全和无害化技术转让、合作和能力建设”作了专门规定[2]。通过有关技术性环境安全的各种国际条约,许多国际组织都卷入了与环境安全有关的事务,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卫生”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化学品和残毒”、联合国救灾协调办事处的“自然灾害”、世界劳工组织的“劳动环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与运输”、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发展计划和合作的环境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联合国开发署的“技术合作”等。著名的国际化学品安全署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三个组织合作开展活动的机构。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迄今已经制定诸如《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56年)、《农药安全使用规定》(1982年)、《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1982年)、《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1985年)、《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年)、《矿山安全法》(1992年)、《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等有关技术性环境安全的政策文件和和法律法规。我国《标准化法》(1988年)明确规定:对工业产品的安全应制定标准;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劳动法》(1994年)对“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有关劳动安全卫生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管理这类安全的政府机关或组织主要有公安部门、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军队警察、安全理事会等组织。笔者将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由于与国家管理、军事行为和政治决策有关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会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产生各种有害影响,人们开始将安全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这时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国际和平、国家安全的有害影响,即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这种环境安全仍然是指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国家社会管理秩序传递不安全影响的中间物即介质。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政治化和社会化以及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态度的转变,一些社会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赋予环境安全以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新的含义,即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地球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确认环境不安全也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有害影响。这样,环境安全就成了一种与原有的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的安全概念;当然,这种环境安全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政治性安全的范畴。
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由于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有害影响,因而在对外交流时宜译为译为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security。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二、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的主要观点和问题
目前,有关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的观点和热点问题很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第十一章“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3],对当代流行的政治性环境安全的观点作了比较全面而扼要的介绍。美国能源部的环境安全中心(U.S. Department of Energy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国家安全政策分析办公室(U.S. Department of Energy
第一,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威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自1960年福斯特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世界末日:公元2026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论文以来,有关地球安全的警钟越敲越响。目前,滥垦滥伐和危险废物使世界满目疮痍、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导致热浪袭击全球、洪水漫延大地,酸雨和放射性污染有如“无形杀手”,臭氧空洞和海平面上升犹如“天塌地陷”,海洋污染使“生摇篮蓝”垂危,热带雨林消失使“地球肺部”受损,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正在夺走人类赖以生存的良田沃土,物种锐减使人类相依为命的“朋友”越来越少,环境致变、生物工程和无性繁殖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人口的增长使人类对未来忧虑重重,地球犹如茫茫宇宙中的一叶负载过重的孤舟,越来越显得弱小和垂危。这种严峻形势是促使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问题的基本动因。
第二,环境问题是国家外交、安全、军事部门不得不认真考虑和对待的和平、安全问题。海洋污染、公海资源分配、越境污染(包括跨国酸雨、越境废物转移等)、南极保护、臭氧层保护等问题,无不涉及多国的利益,弄得不好都有可能引起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事实说明,环境问题和环境压力是引起国家间冲突和政治紧张局势的所有起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是催化剂。国家间常常为争夺原材料、能源、土地、河流流域、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环境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武装冲突。随着资源的减少和竞争的加剧,这种冲突也可能加剧。在许多国家存在着环境压力造成的特别危险:难民的大规模迁移,对稀少水源、肥沃土地、石油和原料矿藏以及有争议的边境的争夺等等,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环境退化正在成为政治动乱和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美国气候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土地退化、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造成的土地减少是使环境难民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未来的15年内,地球上的环境难民人数将在目前的2500万的基础上增加1倍即达到5000万;与之相比,目前受政治、种族或宗教迫害的难民只有2200万。环境难民的大规模的迁移可能表现为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河水的争端已发生在北美(格朗德河)、南美(拉普拉塔河和巴拉那河)、南亚和东亚(湄公河和恒河)、非洲(尼罗河)和中东(约旦河、利塔尼河和奥龙特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1986年,因将富克兰德-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海域宣布为专属捕鱼区而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和阿根廷的关系。阿拉伯各国素以“兄弟”相称,但生命攸关的水资源之争却使他们反目为仇。一些阿拉伯理论家甚至认为,4次中东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都是争夺水资源[4]。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时曾宣称,埃及将绝不会再次首先发动战争,除非为了保护水源。约旦国王候赛因也宣称,除了因为水资源问题,约旦不会再同以色列交火。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已直言不讳地对水源问题可能引发中东战争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认为非洲和中东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对这个地区构成的威胁同任何政治战争所构成的威胁一样大[5]。随着全球人口膨胀,有限的洁净水源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对水的武装争夺越来越不可避免。正如英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宾·蒂凯尔先生说:“水恐怕会比石油这个世界招致更多的战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姆斯·皮克林在1989年指出,正当东西方之间冷战呈缓解趋势的时候,如果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的话,“生态冲突”将会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因而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出席臭氧层条约谈判的代表曾说过:东西方冲突的危险已因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的环保问题而黯然失色。[6]
第三,传统的国家安全活动和军事部门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战争和军事活动是产生严重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源头。在影响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的武装冲突中,热核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将是最严重的,核战争及其所造成的核污染可能给人类留下一个荒芜的星球。另外,常规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伴随战争和难民的大规模迁移而出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瘫痪,对环境同样起着破坏作用。因研制、生产、试验核武器,已使前苏联“丧失”了15%的领地,成为人们无法居住的区域。战争不仅仅导致亿万人生命的丧失和巨额财富的损耗,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在海湾战争中,炸燃科威特的227口油井,燃烧的浓烟严重地污染了大气;还有3.15亿加仑的原油泄入海中,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同时,由于输油管的破裂,在海港区域残留着7500万余桶原油,形成数百个石油湖污染着环境。诚如《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所指出的:“战争定然破坏持久发展。因此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促进其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国家军事、安全部门在保护环境和保育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例如,美国社会已经认识到,美国国防部在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美国国防部给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于环境安全的年度报告(1995年)》[7]的第五部分“环境安全的防护管理”(Part V Defens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ecurity),国防部控制着2500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土地支持着维持战备的基本的军事活动,包括军事训练、试验和作战演习。这些土地也支持着国家重要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例如:在200多个军事设施所在地生活着300多种濒危物种;国防部设施内的数百种财产列入了国家历史登记册;国防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联邦考古收藏品;许多设施拥有土著美国人的埋葬地和宗教地址。国防部环境安全执法规划(the Department""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compliance program)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护美国武装部队的战备,同时又要满足美国和国外的多样化的环境、安全和职业卫生的要求。
第四,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观念必须改变。传统上理解的国家安全概念,即从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有许多弊病;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国家安全和优先问题的认识,把环境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摆在显著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政府往往根据传统的安全定义选择其保障安全的军事、间谍和外交行为,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国家不惜扩军备战、企图通过发展毁灭星球的核武器系统来实现安全上。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将花在军备上的钱与花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上的钱加以比较,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认识到,深重广泛的环境危机给国家的安全,甚至生存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比起装备精良、虎视眈眈的不友好的邻邦的威胁还要大;而绝大多数受害的国家政府,在保护其人民免受侵略军危害方面所花的费用,远远超过了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所花的费用。
第五,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核心观点。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需要”和“限制”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正是人们的一种基本需要,同时也是对重大环境问题的强制性限制。
第六,政治性环境安全观的形成,对防务活动、外交事务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由于环境安全问题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许多新特点,由此推动了环境外交政策和防备环境安全政策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应当考虑研究制定‘环境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这样的事实,即它的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公共区域的环境资源基础有日益扩大的影响,正如其他国家的政策对它们也有影响一样”[8];“各国政府都应研究制定一个‘环境外交政策’,作为改进对各国环境政策的国际协调的一种主要方法。”[9]对环境安全的威胁只能由共同的管理及多边的方式和机制来对付。对“环境不安全因素”没有武力的解决办法,要解决环境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和发展环境外交与国际环境合作,环境外交将为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环境优先而做出贡献。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事部门和武装部队,如果真的关心国家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正确对待和积极解决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等不安全问题。
第七,确保地球的安全和生存取决于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和机构体制改革。从保障环境安全的思想出发,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建立国际环境安全理事会、维持环境安全国际警察部队(即绿盔部队)、国际环境法庭和仲裁庭、全球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等建议和改革办法。目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军备竞赛与环境”已经成为处理政治性环境安全的一个重要国际机构。环境重大技术应该是能够大大减少和减轻环境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技术,要保障国家和平与安全必须将重大环境技术纳入国家安全技术的清单。为了减少环境压力给人类带来的威胁,需要从全球范围重新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这种重新确定要求广泛地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安全评价方法,特别是环境风险评价,而且包括军事、政治、环境和其他方面的争端。对不可逆转的自然系统的破坏及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全的威胁的鉴定、评价和报告的能力,应予以加强和扩大。
第八,深入开展环境安全的理论研究,明确环境安全的概念、分类、性质、特点、目标和组成要素,树立正确的环境安全观。有关国家主权、国防、外交和军事等国家安全系统的环境安全,一般可以分为地方环境安全(包括社区环境安全)、国家环境安全、国际环境安全(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的环境安全)等不同的层级。在安全领域,目前正在认真研究环境安全的定义、种类、性质、特点、环境安全分析、环境风险评价、非传统的威胁(un-conventional threats)等问题。不同层级的环境安全有不同的目标。例如,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环境安全规划》,美国的环境安全有4个压倒一切的、相互联系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符合环境法律。第二个目标是支持美国武装部队的战备、保障武装部队能持续地进入其军事训练和试验所必须的水域、陆地和空间。第三个目标是改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免受环境、安全和健康方面的危害,并维持军事设施的质量。第四个目标是促进改善武器系统的性能、降低成本、提高其环境性能。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explosive 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污染预防,是指尽可能地在源头制止污染,以及合理的管理、再循环或处置潜在的污染物;技术,是指更有效、更节约地实现国防部的全部环境安全目标的技术;安全和职业卫生,是指平民和军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和健康保护;自然保育,是旨在保护和保存经公共委托的由国防部所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自然保护;符合法律,是指保障国防部实施的活动坚持环境安全、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实行净化,是指恢复国防部(被污染)的设施,降低来自被污染场所的风险;爆炸安全,是指防止爆炸事故,保护人民、设备和设施免受事故性爆炸的影响;害虫管理,是指保护国防部人员免受昆虫媒体所传播的疾病,保障害虫控制方法的合理应用。
第九,深入研究环境安全的具体政策问题,制定正确的环境安全政策和规划,将环境安全工作法定化、制度化。由于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不断深化,原来的外交政策制定的方式在迅速发展,并且正在对国家的国内行为方式逐渐增加影响。为了减少人类的灾难和财政花费,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努力研究冲突的根源、从事预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这种主动对待外交政策制定(this pro-active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making)的一个范例,就是对环境压力和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21世纪议程》强调:“应当考虑采取符合国际法的措施,处理在武装冲突中对环境造成的依据国际法说不过去的大规模的破坏”;“鉴于非常有必要确保核发电安全和无害环境,并且为了加强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当努力完成当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持续进行的、拟订一项核安全公约的谈判”[10]。为了发展环境安全技术,确保环境安全,美国《环境安全规划》非常重视环境安全技术问题。该规划中的环境安全技术是指先进的能够改善防务环境安全(defense environmental security)的各个方面的技术,包括:在源头防治污染的更大的能力;更加富有创造力的自然保育创新能力;符合较低成本;更快、更便利、更有成效的净化。国防部的环境安全技术方面的战略是:配备与国防部实际需要相称的环境技术投资;查明能够提供回报的技术;鼓励创新的双重使用(dual-use technology)技术的发展;加快这些技术的利用和商业化。
第十、研究环境安全与相关问题的关系。在环境安全与环境外交关系方面,主要研究各种处理环境安全问题的和平方法、环境安全国际纠纷的调处、环境安全国际条约的制定与履行等。在环境安全与国防关系方面,主要研究战争行为、军事活动、武器试验、军事场所等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在环境安全与国际环境合作方面,主要研究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的建立、环境安全信息情报的搜集和传递、重大环境安全技术的评价、应付国际环境不安全事态或环境风险的国际机构与处理办法、环境安全的国际合作机构和管理体系。在重大领域的环境安全问题方面,主要研究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越境酸雨、危险废物越境运输处理、环境致变技术、生物工程基因致变技术、南极环境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公海环境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等。
三、环境安全从观念到实践的发展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国家安全立法,并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安全立法,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法》(1947年)、《巴西国家安全法》(1953年)、《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法》(1991年)等。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一些国家已经将环境安全纳入本国的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安全政策范畴。
从国际范围看,将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将国际环境保护提高到国际安全的高度、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国际安全的议程,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进步。近年来,有关政治性环境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逐步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策和法律文件提到或论及环境安全问题。以至有人预言,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体制为核心的安全体制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较早将环境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明确联系起来的重要国际环境文件是《内罗毕宣言》(1982年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该宣言指出:“一种和平安全的国际气氛,没有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不在军备上浪费人力物力,也没有种族隔离、种族分离或任何方式的歧视,没有殖民主义和其他方式的压迫和外国统治,对于人类环境将有极大的好处。”接着,《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大会1982年10月28日通过)不仅提出了政治性环境安全的思想,而且已经将防止自然免受军事活动和其他敌对活动的有害影响作为自然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宪章规定的第五项“基本原则”是“必须保护自然免受因战争和其他敌对活动所引起的破坏的危害”;从政治性环境安全的角度看,该项原则含有“应该将环境问题与战争、敌对活动等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的意思,这里的“保护”环境是安全保护的保护(secure)。这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中的第25项原则,即“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储存和不可分割的”[11],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这次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1992年6月)已经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一个“安全的”多边贸易制度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等环境安全问题联系起来。通过这次会议,加深了各国对环境安全的危机感。另外,国际社会已经通过许多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的条约,如《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3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1976年)、《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年)、《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1986年)等。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策和法律文件提到或论及环境安全问题。
环境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环境安全观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际和平和国际政治的含义,不但政治在绿化、政党在绿化,国家安全和外交也在绿化。全球的公共资源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管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对付整个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并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例如,据1994年10月13日《中国环境报》消息,肯尼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6个东非和南非国家,于1994年10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签署了《卢萨卡协议》。该协议规定,由各签字国组成一个具有国际执法机构性质的管理委员会,在这个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野生生物特别武装部队,负责追捕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非法贸易的偷猎者。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国际环境警察部队,签署协议的上述6个国家将为这支野生生物特遣部队提供人员,加拿大、丹麦、挪威、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将为这项新方案的实施提供财政支持。为了加强对国际环境安全的管理,根据“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际发展委员会”和“裁军与安全委员会”等联合国委员会在1989年召开的会议的决议,在1991年制定了一个叫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共同责任:关于全球安全和管理的斯德哥尔摩动议》的文件;根据该文件,经联合国秘书长批准于1992年成立了一个由28个成员组成的“全球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于1994年编制的报告[12]指出:“全球管理的发展,是人类组织地球上的生活的工作的进程的一个部分,并且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公共交通站。……我们正处在全球管理需要启动和革新的时代。”该报告呼吁“对所有国家的传统的发展方式进行根本的改变”,提出了在联合国建立“经济安全理事会”(Economic Security Council)的建议。对国际环境安全重视的一个标志是国际法院于1993年设立了一个新的环境庭(Environment Cha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用来处理环境事务。根据宣布新厅成立的报告[13],之所以设立新庭是由于认识到环境法在过去几年的迅速发展,国际法院需要准备尽可能充分的环境案例。该厅严格限于国家之间的环境案件,只有国家才能提起诉讼;法院的管辖权受到限制,只有纠纷当事国表示愿意接受管辖时,国际法院才有管辖权。对此,有些国际组织和个人已经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在1990年,意大利最高法院的法官Postiglione曾经建议在联合国体制内成立一个国际环境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the environment),该建议立即获得一些政府组织和个人的签署同意。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联合国国际法院不是审理环境事务的合适场所,这就要求一个专门法院;该法院应有广泛的管辖权,不能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案件,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机构,以及有关个人或者受到相应环境退化损害的个人也可以提起诉讼。[14]
在冷战结束后重建国际秩序的背景下,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获得广泛传播。诸如环境破坏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优先问题,并且促进了国际法的成熟;与此同时,日本已经提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焦点之一”的观点;俄罗斯已将“和平、生态、裁军、经济问题通盘考虑”;美国已将其环境考虑纳入其外交政策之中。在国际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机构,也是处理环境安全问题的机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1977年)第5条明确规定:“关于任何一个缔约国破坏行动的控诉,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安理会必须进行调查。”近几年来,因战争、军事行为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国际环境外交问题已相继出现,该理事会做出的有关海湾战争和对伊拉克制裁的决议中,已经涉及环境安全问题。例如,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环境破坏,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 87号决议指出:“依据国际法,伊拉克对任何直接的损失和破坏负有责任,包括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损耗……因为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是非法的。”这是联合国做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战争所引起的环境破坏赔偿问题的第一个决议。接着,安理会于1991年5月通过第692号决议,成立了赔偿基金和赔偿委员会,确定了伊拉克应予赔偿的项目和赔偿基金;据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94年成立了一个环境破坏、责任和赔偿的专家工作组。
在国防环境安全方面,进入本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国防方面的环境安全问题。为了保证美国军队的和其他的联邦设施都符合作为美国支撑的同样的法律,依靠两党的大力支持,美国国防部(the U.S. DOD)的环境安全规划(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Program)在1980年代逐步形成。在1984年,里根总统签署了“防务环境恢复报告”(the Defens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ccount(1984)),促进了环境安全方面的政策。1986年通过的《超级基金修改和重新授权法》(the 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86),明确要求联邦政府包括国防部遵守并完全实施平民的环境净化标准(civilian environmental cleanup standards)。在布什政府时期,国防部长切尼(Cheney)在1989年给各军种部长的一个备忘录中,清楚地说明了环境安全规划的基本内容。他说:“我要求国防部成为联邦机关中遵守环境法和保护环境的先行者。为了对国家环境议程(the Nation""s environmental agenda)负责,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承担义务。我要求每个指挥官都成为评价联邦官员的环境楷模。”1993年,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佩里设立了一个负责环境安全的国防部长助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美国能源部建立了的环境安全中心(U.S. Department of Energy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国家安全政策分析办公室(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Off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alysis)。美国环境保护局也成立了专门研究环境安全的机构。在1994年,国会通过了《环境安全技术检验规划》(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为在军事设施方面的技术合法化以及由私营工业和联邦机关作示范提供资助。同年,国防部与私人部门一起工作通过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标准》(National Aerospace Standard)、《有毒物质管理规划》(Hazardous Materials Management Program),建立了可以在真实条件下测试清洁技术的具有工业规模的示范工厂;建立了有毒物质管理制度,广域防务自动网(a defence-wide automated network)。在1995年,国防部继续把环境安全考虑纳入到武器系统的制造、维护和操作的所有方面,并实施了一个“三军环境质量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a tri-Servi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为了执行国防部的环境安全技术方面的战略,《国防部环境安全技术规划》(the DO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echnology Program )建立了一个对整个军事部门的环境技术研究和发展项目进行协调、综合和优选的程序。他们的目标是强调和强化防务机关和武装部队的环境工作,将环境安全全部纳入到美国的防务任务之中。目前环境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国防任务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防务的最重要一项任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美国已从单纯关注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军事对峙的传统外交目标和政策向环境外交方面做出重要的战略调整,已经将环境问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将环境目标纳入其长远的外交日程和国际战略目标之中。1996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1世纪全球的环境挑战》的讲演,他提出:“在克林顿总统及戈尔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政府开始认识到,我们能否发展自身的全球利益与如何利用地球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决心给予环境问题应有的地位:即置其于美国主要外交政策之中。”该讲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构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概念。此后,美国开始有计划地在外交领域打“环境外交牌”,并于1997年开始每年发表世界环境报告,利用环境外交对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环境资源状况进行评论和指责。
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环境外交活动,各国日益重视环境外交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环境外交的理论研究日益活跃,有关环境外交的刊物、论文和著作逐年增加,一批职业环境外交家和环境外交学者应运而生。1983年,美国密执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环境外交:对美、加越境环境关系的回顾和展望》[15]。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各国政府都应研究制定一个‘环境外交政策’,作为改进对各国环境政策的国际协调的一种主要方法。”[16]198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际环境外交》论文集[17]。19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臭氧外交:保护星球的新方向》[18]。
在我国,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已经制定包括《国家安全法》(1993年)为主的一整套国家安全法规。但是,这种国家安全或安全法规很少考虑环境安全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很少明确规定环境安全问题,但是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已经将某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和资源的行为纳入社会治安管理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对环境安全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和深化。江泽民主席1996年7月16日《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确保环境的安全,必须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现在,环境问题已经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要注意防止国外有些人把污染严重的项目甚至‘洋垃圾’往我国转移,切不可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危害子孙后代”[19]这一讲话,已经将环境安全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目标,已经注意与环境安全相联系的环境外交,已经将环境问题与国际政治、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和环境外交联系起来。目前,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有关的环境外交政策,并已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环境外交活动。有的国家领导人在有关讲话和文章中已经将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提高到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即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解放军已经将军队环境保护工作提高到相当的高度。有关环境安全和环境外交的学术论文日益增多。
[1] 蔡守秋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1992年6月3至14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4] 见1992年2月15日德国《商报》文章“中东问题的主要症结──围绕水资源的斗争”。
[5] 见1991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文章“天生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6] 见1997年4月12日中国环境报。
[7] An Annual Report from the DOD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of the U.S.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William J. Perry Secretary of Defense February 1995, 国防部长威廉 J·佩里。
[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9] 同上,第413页。
[10]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11]《中国环境报》1992年7月2日。
[12]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
[13]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onstitution of a Chamber of the Court for Environmental Matters", Communique No 93/20, 19 July 1993; se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993) 4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776-7.
[14] See: Amedeo Postiglione, "A More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Environment an d Setting Up an International Court for the Environment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1990) 20 Environmental Law 321.
[15]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An Examination And AProspective Of Canadian-U.S.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16]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17]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edited by John E. Carro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Ozone Diplomacy: New Directions In Safeguarding the Planet, Benedick, Richard Ellio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19]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第3~5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最新推荐
猜你喜欢
-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工作要点
- 公司经理助理实践感想--实习经历
- 2023年竞选班长演讲作文(五篇)(精选文档)
- 2023年度最新舞台叙事作文素材优秀
- 在全区民政残疾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讲话
- 经济薄弱村情况汇报材料
- 2012年上半年医院重点工作情况汇报
- 致消费券单位的感谢信
- 最新雨过天晴记叙文作文优质
- 防踩踏演练活动总结
- 建设新农村繁荣群众文化下乡文艺汇演主持词
- 纪检委廉政建设快板征文
- 我心爱之物风铃作文600字左右汇总(全文完整)
- 公诉科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小结
- 劳动争议类案件立案之思考
- 街道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 2005年稽查大队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
- 2022年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事迹材料
- 残联年度工作总结精选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