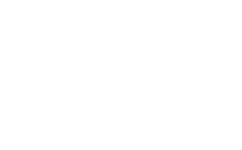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政策”是我们用以理解中国农村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农村,正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完成着农村社会的整合,维持着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支持着国家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意图和努力,政策指导着农村生产的开展和生活形态的构造,并最终决定着包括物质财富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分配方式、过程与份额。这样,“政策”就成为农村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控制性因素。
在实地的农村调查和研究中,我经常会问及农民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政策好不好”?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国家政策很好”;那么既然国家政策很好,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农村面貌没有太大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有明显的提高呢?得到的回答也是一致的,“都是干部的问题,是干部人为地把好政策给执行坏了”,即所谓“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当我们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基层党政干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相反的,干部们会说,这种政策别说我来干,就是让农村研究专家来干,让总理来干,他也干不好。在干部们看来,农村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其本质的和主要的原因并不在干部和基层政权,而是国家政策本身就有问题。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回答会使一个认真的研究者感到十分迷惑,如果持完全相反意见的双方都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成了一个“谜”。
乡镇政府所实行的一些办法和措施在许多时候被当作“土政策”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看待,这些行动从可观察的层面上看明显地违反了国家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从而被广大农民和学者们所“痛恨”,成为“好政策被干部们执行坏了”论点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证据。如果我们发现诸如农业特产税平摊这样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极为普遍,操作手法或许不尽一致,但在逻辑上却具有高度一致性,就会知道如果将如此大范围且高度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规则和行动称之为“土政策”是不甚妥当的。无疑,这些行动是与国家政策——以明确的文本形式所规定的政策——相抵触和相冲突的,但为什么这些“明显违背政策”的行动和行动模式会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呢?这必须从基层政权和干部对政策的理解来解释,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深刻地“理解”这种理解。
我们知道,特产税平摊等办法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直接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由于特产税平摊不符合国家政策或者“违反政策”而被人们所关注,而正是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才被注意到,或者说才使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也就是说,人们(包括中央、民众和多数学者)关注的并不是基层政府的某种行动和由这种行动所生产出的结构是否违背政策文本,而更倾向于从其后果来进行评价,如果其后果是积极的,那么这些行动就是被默许乃至允许的,反之就会被加以各种形式的抨击。这一评价机制本身就已经暗含了导致产生“政策不好还是干部不好”争论的根本逻辑,同时也正是政策在农村实践过程的逻辑,更是农村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本逻辑。
农民负担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水面”,由于特产税分摊等办法的普遍实行,在90年代以后迅速加重。随着农民负担问题的日趋严重化和表面化,中央政府的态度发生着明显的转变。在1985年农民负担问题仅仅是“消极因素”,1993年定性为“政治问题”,到1999年,已经将其定性为“重大政治任务”,对中央政府来说,农民负担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政府的长远利益,不仅影响政府的经济目标,而且也威胁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批评措辞也日渐严厉,惩罚力度逐渐加大。按照惯常的思路,在中央政府如此严重的关注和如此严厉的批评下,基层政府的行为应当大为改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各地各种研究都在证明,乡镇政府的行动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违反了国家政策文本的规定。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们来详细分析“解读”一些中央政府的文件规定。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99年上半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等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十分关注,也十分清楚,甚至在中央文件中极为详细而且明确地指出“严禁到农户家中拉粮食、牵牲口、搬家具”。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不可谓不细致,更不能以通常用来指责政策制定“笼统”“原则性的”这样的词句来描述它。但为什么就没有起到作用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些文件的另外一些章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99年上半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中指出:“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大局、讲政治的高度,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确保本辖区内不发生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凡是发生严重事件、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的地方,县、乡党政主要领导不得提拔重用,实行一票否决。凡是由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不到位,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恶性案件的,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还要追究上一级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凡上报不及时、查处不得力,致使案情恶化,甚至引发新的事端,影响农村稳定的,要追究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中指出:“对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而引发严重群体事件和恶性案件的,除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以外,还要追究市、县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对屡次发生涉及农民负担严重群体事件和恶性案件,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性质特别严重的,要对省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责任人给予处分”。
详细解读以上文件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央政府最关注的,不在于农民负担是否在加重,情况到底严重成了什么样子,而在于“确保稳定”,在于“不出现严重群体事件和死人恶性案件”,因此,“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大局、讲政治的高度,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确保本辖区内不发生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 对屡次发生涉及农民负担严重群体事件和恶性案件,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性质特别严重的,要对省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责任人给予处分”。也就是说,这些文件对于干部的意义在于:只要没有出现严重群体事件和死人恶性案件,这个地区的农民负担就不算十分严重,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容忍的,这个地区也就大致可以看作是稳定的。而只要是“稳定”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也就是“能从大局出发,是讲政治的”,因而也就是基本合格的官员。至于在“稳定”的表面下究竟是什么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这给地方政府一种强烈的暗示:中央政府评价的标准在于“政治影响”,在于在50周年大庆等特殊时期“不出事”,因此只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行事就是安全的,不管这种行动是否在事实上违反了中央政策,只要是没有出现恶性事件,那么就没有突破政策的框架。干部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政策:加重农民负担、使用非正常手段都是被默许的,只要不出事就可以,因此关键不在于减轻农民负担,而在于在使用这些手段的同时如何控制恶性事件的发生。在我所做调查中所复印的这几份乡镇政府存档的文件中,都在“严重群体事件和死人恶性案件”字句下面画有表示着重的横线,这大概能够反映基层官员对于中央政策关注点的“心领神会”。
而我们更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心领神会”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为什么基层政府会如此普遍地同时是极为一致地来这样“理解”和“解释”中央政策?这种机制是什么?
“变通”是对此最富解释力的一个概念。实践中处处可见变通的痕迹。在调查中我们见到的《中共C县委、县政府关于用足用活国家政策全力加快经济发展的通知》中讲到:“中央12号文件和省委17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政策措施,在经济工作指导上转向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高度重视,将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用足用活国家政策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来抓,抢抓机遇、加大措施,确保搭上这班车……每个项目班子要迅速行动起来,跑部、进省、到京,争取有关部门支持,能争一点是一点,能争一项是一项,凡是有希望进入国家、省“笼子”的项目,要靠在有关部门连续做工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中间的“用足用活国家政策”、“跑部、进省、到京”、“要靠在有关部门连续做工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究竟在实践中会是怎样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要采用哪些合法与事实上甚至非法的手段来争取项目和资金,干部们是非常明白的。县委县政府这样明确要求了,这样去做自然并没有错,而且“争取到国家、省、市无偿拨款,按拨款额的1-5%奖励有关人员”,也就是说,变通,无论是什么手段和方式的变通,只要能够完成当前的阶段性任务,就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而那些不能够有效和自如地使用变通手段的干部则被视为“无能之辈”,要“向县委县政府说明情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变通成为日常的、必须的工作方法、思路和模式。从逻辑的一致性上来说,既然在这一方面变通是被允许和鼓励的,那么在其他的方面也应当是这样。从干部的心态上来讲,既然这些事实上违反政策甚至违法的变通行动(比如在争取项目和资金过程中的请客送礼甚至向关键人物和部门实质上的行贿)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政策并不是不可以违背的,甚至还是被自己的上级所鼓励的一种行动,关键在于后果,在于产生“有效益”的起码是不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后果,而一旦后果是“有效益”的,似乎国家政策也就没有被违反,因为毕竟在一定范围之内达到了中央和上级所要求的“经济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目标,这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贯彻执行了中央政策精神,怎么能说是违反了中央政策呢?这样看来,政策实践过程中中规则不是在事先作为约束而存在的,而只是在行动中和行动以后使行动成为可说明、可解释的工具。
从更加深入的层面看,中央政府并未对地方政府许多方面的变通行为实施制约和批评,而且是在事实上鼓励这些行为,甚至中央政府自身的许多行动也是以变通的方式来进行的。中国渐进式(目标开放式)的改革路径决定了改革必然要在给定的意识形态——一种给定的结构和情景——条件下进行,这样就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争论,比如在对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等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中央政府必须在保持意识形态方面合法性和连续性、稳定性——这是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基础——的同时,实质上推进市场转型的进程。这种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思维方式和实际上的工作策略必然地会贯穿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的行动中,实质上的变通成为各级政府行动的重要内在逻辑。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的变通往往是受到中央鼓励的,比如山东诸城市率先开展的把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卖掉甚至送掉的行动,江南一些地方前些年积极扶持私营企业的行为等等,这些在当时的政策文本范围内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可以视为“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此后都得到了承认并且被中央政府大力推广,并被解释为“首创精神”。这些明显违反政策的行动受到中央当时的默认和事后的奖赏,不能不使干部们对政策文本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对中央政府的各种提法产生怀疑,这样,中央政策再严厉的三令五申也会在这种怀疑当中大打折扣,因为实践证明政策是可以违背的。按照这样的理解逻辑,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过程会是怎样可想而知。
改革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也许还可以加上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理论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以及在实践中的创造和“再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的变通、扭曲的出现,同时也导致中国学习西方的法制化进程——形式理性的生长——不能够顺利展开。
结合以上所述,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是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变通行为只不过是在表面上违背了政策文本,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却十分契合政策本意——渐进式改革鼓励变通的根本性逻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变通行为才能如此大行其道而未受到国家真正严厉的、有效的禁止,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过程才会充满着各种各样“创造性的行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新的结构模式。与此同时,国家也正是利用基层政府的变通性和创造性行动来完成自己渐进式改革的总体目标,这是国家一种“隐秘”的需求。实际上,在中央和基层政府间实行的,是共同的行动逻辑和相近的治理原则,而不是相反。这要求两者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理解、默契和配合。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对具体问题理解角度和程度不同,以及行动“脚步”快慢不同,并不总是能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舞伴”。
以上所分析的是基层政权和干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当然他们不一定是这样清晰且理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其思维和行事的逻辑是这样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却不会从这个意义和层面上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一方面,农民倾向于以朴素的方式,从字面上理解政策文本,中央政策既然三令五申不得加重农民负担,那么这就一定是中央政府清楚且真实的意思表达了;上级文件严令税费不得在农户间平摊,如果最终乡镇政府和村级干部还是将任务平摊了,那么就一定是“政策很好而干部很坏”,一定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另一方面,农民个体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大众媒体)见到了中央政策文本,了解了文件的内容,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一过程,他们只看到初始的文件与最终的结果,“好政策”与“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不能不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政府和干部们痛恨不已,抵触情绪加剧,农村地区也就变得更加动荡不宁。而基层政府要在这种局面下还能够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控制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进一步实施过激的行动,一个恶性循环有可能就开始了。同时也正是由于干部和农民对政策文本理解上和判断逻辑上的巨大差异,导致本文开始时指出的双方对“政策不好还是干部不好”这一问题的完全相反的回答。
在考察农民上访问题时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逻辑和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中央和上级一再做出的“维护农民利益”的声明和政策表达给农民以集体越级上访的激励和解决问题的希望,上级和各种媒体(在农民看来媒体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同时也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一再做出的对基层政府的抨击和指责又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自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而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是站在自己和中央政府的对立面上在胡作非为。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地方政府做任何的开脱和解释,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的“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出现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权的声誉和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基层的权威和合法性则又一次被削弱。与此同时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前提下,面对那些自认为“受到上级和中央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起来的农民,农民有可能以越级集体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认为是对自己权威的又一次挑战,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去找“来自上面的光”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又开始了。
干部和农民对于“国家政策”以及对政策实践逻辑的理解的巨大差异导致在两者之间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们之间的对话更像是是“自言自语”。“干部不好还是政策不好”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能只在政策制定和干部作风上面找寻答案,而应当反省整个农村地区的治理结构、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长期形成的改革逻辑,反省干部们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方式的原因,这可能比看似具体而实际地谈论精简乡镇机构、取消乡镇政权等还要实际得多,这是“触及灵魂”的反思。